赵莉散文欣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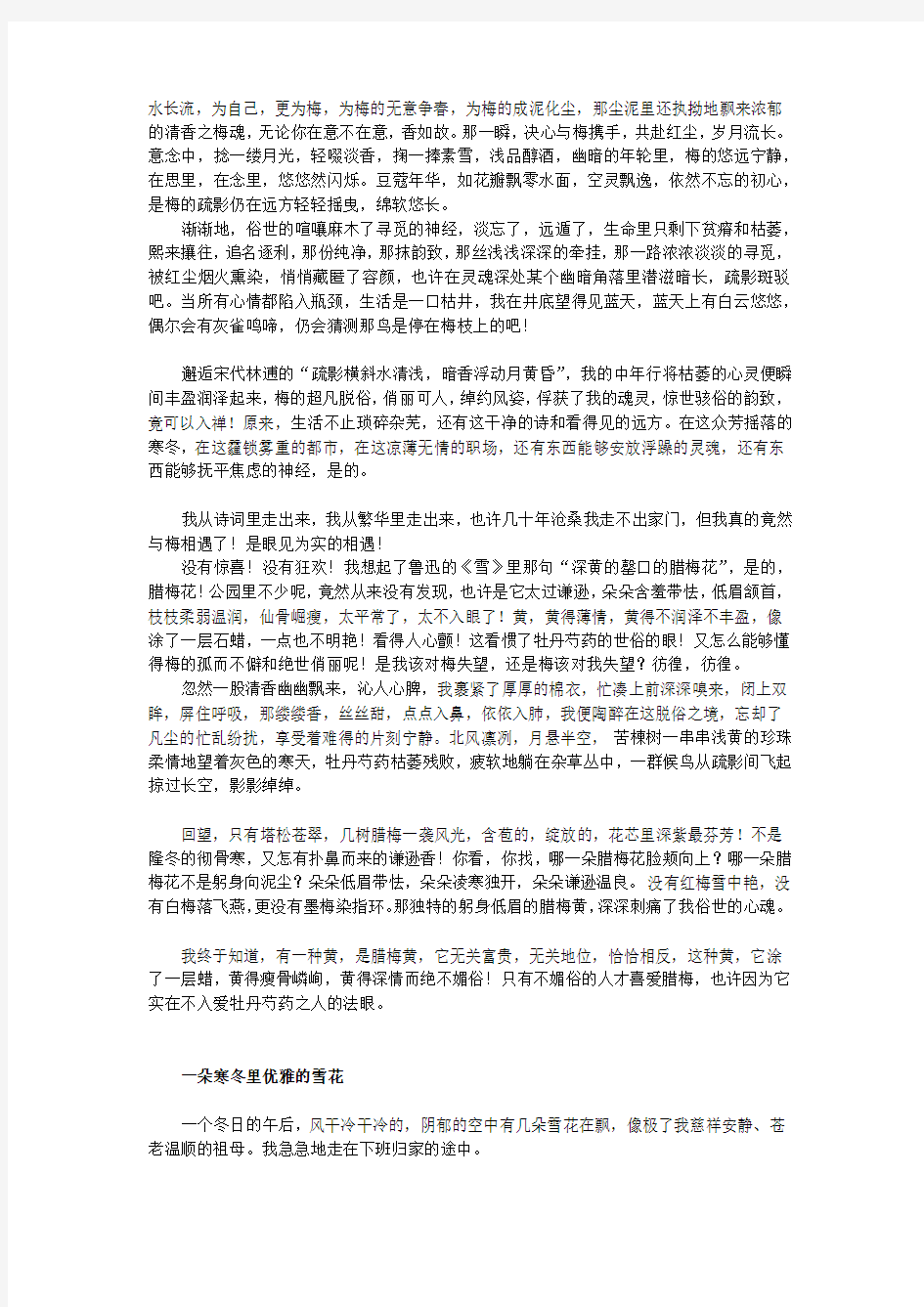
渭北文集之春卷——
《兰亭诗语》散文欣赏:
新锐作家简介:
赵莉,网名四月天,渭南市经开区中学语文教师,渭南市诗词学会会员,七律《冬赏天鹅湖天鹅》被收入“天鹅杯”全国诗联大奖赛作品集《天鹅之恋》中,七绝《荷语》三首发表在《西岳》杂志,现代诗歌《无题》、《今夜,你想你了》等发在《三贤文苑》。散文作品多呈现在网媒和文学平台。
暗香疏影觅红尘
情牵梅花三生,只因在千年诗词里品其神韵,水墨丹青里睹其芳姿,心之所向,神之所往,红尘滚滚,韶华流年,我竟无幸与梅相牵,心生几许遗憾,几多渴盼。
儿时,感动于课本里那一株梅花,粉嫩的朵儿,惊艳了整个童年。“墙角数枝梅,凌寒独自开。遥知不是雪,为有暗香来。”王安石的《梅花》,给了一个偏僻村落的贫苦小女孩多少美丽的向往啊!谁曾知道,她寻寻觅觅,脚步遍及村里角角落落,却没有梦中梅花的踪迹。雪花飘,寒风吹,树树烟色月如灰,草色冷青隐枯翠,梅香斜倚梦中飞。
十一二岁,惊讶于毛泽东的那枝梅花。“已是悬崖百丈冰,犹有花枝俏,俏也不争春,只把春来报。待到山花烂漫时,它在丛中笑。”那颗少女的心,瞬间被寒冰悬崖的朵朵俏丽深深打动,笑傲寒霜向小园,百花摇落独暄妍。梅的内敛,梅的谦逊,梅的孤而不傲,芳而谦和,让一个妙龄女子多了几许古典的情怀。
十五、六岁,当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年龄,陆游的梅花与我不期而遇。“驿外断桥边,寂寞开无主。已是黄昏独自愁,更著风和雨。无意苦争春,一任群芳妒。零落成泥碾作尘,只有香如故。”梅的寂寞,梅的神韵,梅的风骨,梅的胸襟,便深深扎根在少女的心里,泪
水长流,为自己,更为梅,为梅的无意争春,为梅的成泥化尘,那尘泥里还执拗地飘来浓郁的清香之梅魂,无论你在意不在意,香如故。那一瞬,决心与梅携手,共赴红尘,岁月流长。意念中,捻一缕月光,轻啜淡香,掬一捧素雪,浅品醇酒,幽暗的年轮里,梅的悠远宁静,在思里,在念里,悠悠然闪烁。豆蔻年华,如花瓣飘零水面,空灵飘逸,依然不忘的初心,是梅的疏影仍在远方轻轻摇曳,绵软悠长。
渐渐地,俗世的喧嚷麻木了寻觅的神经,淡忘了,远遁了,生命里只剩下贫瘠和枯萎,熙来攘往,追名逐利,那份纯净,那抹韵致,那丝浅浅深深的牵挂,那一路浓浓淡淡的寻觅,被红尘烟火熏染,悄悄藏匿了容颜,也许在灵魂深处某个幽暗角落里潜滋暗长,疏影斑驳吧。当所有心情都陷入瓶颈,生活是一口枯井,我在井底望得见蓝天,蓝天上有白云悠悠,偶尔会有灰雀鸣啼,仍会猜测那鸟是停在梅枝上的吧!
邂逅宋代林逋的“疏影横斜水清浅,暗香浮动月黄昏”,我的中年行将枯萎的心灵便瞬间丰盈润泽起来,梅的超凡脱俗,俏丽可人,绰约风姿,俘获了我的魂灵,惊世骇俗的韵致,竟可以入禅!原来,生活不止琐碎杂芜,还有这干净的诗和看得见的远方。在这众芳摇落的寒冬,在这霾锁雾重的都市,在这凉薄无情的职场,还有东西能够安放浮躁的灵魂,还有东西能够抚平焦虑的神经,是的。
我从诗词里走出来,我从繁华里走出来,也许几十年沧桑我走不出家门,但我真的竟然与梅相遇了!是眼见为实的相遇!
没有惊喜!没有狂欢!我想起了鲁迅的《雪》里那句“深黄的罄口的腊梅花”,是的,腊梅花!公园里不少呢,竟然从来没有发现,也许是它太过谦逊,朵朵含羞带怯,低眉颔首,枝枝柔弱温润,仙骨崛瘦,太平常了,太不入眼了!黄,黄得薄情,黄得不润泽不丰盈,像涂了一层石蜡,一点也不明艳!看得人心颤!这看惯了牡丹芍药的世俗的眼!又怎么能够懂得梅的孤而不僻和绝世俏丽呢!是我该对梅失望,还是梅该对我失望?彷徨,彷徨。
忽然一股清香幽幽飘来,沁人心脾,我裹紧了厚厚的棉衣,忙凑上前深深嗅来,闭上双眸,屏住呼吸,那缕缕香,丝丝甜,点点入鼻,依依入肺,我便陶醉在这脱俗之境,忘却了凡尘的忙乱纷扰,享受着难得的片刻宁静。北风凛冽,月悬半空,苦楝树一串串浅黄的珍珠柔情地望着灰色的寒天,牡丹芍药枯萎残败,疲软地躺在杂草丛中,一群候鸟从疏影间飞起掠过长空,影影绰绰。
回望,只有塔松苍翠,几树腊梅一袭风光,含苞的,绽放的,花芯里深紫最芬芳!不是隆冬的彻骨寒,又怎有扑鼻而来的谦逊香!你看,你找,哪一朵腊梅花脸颊向上?哪一朵腊梅花不是躬身向泥尘?朵朵低眉带怯,朵朵凌寒独开,朵朵谦逊温良。没有红梅雪中艳,没有白梅落飞燕,更没有墨梅染指环。那独特的躬身低眉的腊梅黄,深深刺痛了我俗世的心魂。
我终于知道,有一种黄,是腊梅黄,它无关富贵,无关地位,恰恰相反,这种黄,它涂了一层蜡,黄得瘦骨嶙峋,黄得深情而绝不媚俗!只有不媚俗的人才喜爱腊梅,也许因为它实在不入爱牡丹芍药之人的法眼。
一朵寒冬里优雅的雪花
一个冬日的午后,风干冷干冷的,阴郁的空中有几朵雪花在飘,像极了我慈祥安静、苍老温顺的祖母。我急急地走在下班归家的途中。
突然,耳畔传来悠扬的二胡声,仿佛喧嚣里的一缕佛音,让这个飘雪的午后干净馨香,温暖盈怀。我循声望去,只见不远处的路边散着几个人,悦耳的音乐便是从那里袅袅地飘来。我走近前去,原来是一对年迈的老夫妻在引弦歌唱。男的腿有残疾,端坐在一旁的小凳子上,一只满是褶皱和裂痕的老手在简易的褐色二胡琴上左右挥舞,另一只手灵巧地拨弄琴弦,琴弦很细,最下面那个筒状的音箱看上去还不错,流淌出缠绵凄切的琴音,让人顿觉心灵澄澈。女的上身穿着臃肿破旧的灰蓝色棉袄,头上还包着过去祖母包头的四方帕,左手拉着一个用来伴奏的破旧的音箱,右手里捧着一个周边有些破损的小瓷盆,里面躺着几张纸币,皱巴巴的,有两元的,一元的,五角的。我没有看见谁投给她钱币,人们都急匆匆赶路或者做生意,只是偶尔驻足观看,但是她依然优雅安静地站着,二胡依然如泣如诉地悠扬着,不时有雪花飘落在她手上的盆钵里。我从包里拿出一张十元钞票,欠下身子,轻轻放到盆钵里。她微微抬起头,给我一个善意的笑脸,说了一句带着外地口音的“谢谢”。
我看到了一张布满皱纹的老脸,浑浊不清的眼睛里闪现出慈悲恬淡的光芒。她的男人,那个腿有残疾的苍老男人,只是埋下头继续挥舞着右臂,好听而熟悉的旋律让商贩们也不由自主地跟着节奏轻哼起来,探出身来观看聆听。巷道里的垃圾纸屑静静地躺着,肮脏的流水浸湿了落雪,路边一颗老树安详地看着这个有些芜杂又有些温暖的世界,周遭若隐若现的洁白的雪朵仿佛来自于彼岸天堂,整个画面像一幅无法临摹的古老的油画。
我不知道这一对异乡的老人此生有过怎样的沧桑,在生命走向黄昏的时光里,不离不弃相持相携在外漂泊,他们的子女又是怎样的人,如何忍心让年迈的老父母去流浪卖唱?难道,是他们以残疾的身体对音乐的痴爱不能让儿孙们接受吗?无论如何,我宁愿相信,他们生命里坚守着一种柔韧与慈悲,一种执著与尊严,因为我从那老女人秋菊般淡然的笑容里读出了骄傲和优雅。是的,即使在最底层里卑微的行乞,他们依然不卑不亢,安静豁达,潦而不倒,相依相守,不离不弃。不管有没有人打赏,他们依然用心地演奏、歌唱,云开云散,雪落雪飘,这一切和两个人长相厮守相比,都是装点灵魂的风景。我们能够给予的,不应该是怜惜与猜测,而应该是灵魂深处的敬重与景仰。在风餐露宿的街头,在无法预知的下一站,他们依然能将沧桑的岁月演绎成明媚婉转的绝妙之音,这份行走在卑微里的优雅娴静,值得我用一生的时间来学习。
二胡声渐行渐远,他们优雅出色地演奏却深深定格在我的脑海里。我想,慈悲的力量是无穷的,困顿的冬天总也有盛开的花朵优雅地飘香。
此刻,我明白了,生命的黄昏里,那份相守不弃永远是美好的,令人感动的。高贵的灵魂,即使偶尔蒙尘流落街头,也掩盖不了她本身奇异的光芒。此生,我亦愿做一个安安静静的女子,在逼仄的世间和相爱的人携手并肩,以慈悲之心优雅从容地行走。
故乡之冬
冬来了,我常常在这样的日子深深怀念故乡之冬。
记忆中,故乡之冬是苍苍茫茫的。渭北平原一马平川,树枝落尽了叶子,冬麦像历尽世事看淡红尘的女子,绿得疲疲塌塌。是谁家的一片包谷杆还倔强地守在褐色的田头,枯萎的叶子耷拉着,似乎仍在絮絮地诉说着曾经的风光。冷风凛然,摧残着这个孕育了万物的世界。
田间的大白菜倒是风光得很,遍地青白整齐地排列着,这是母亲种的。为了让菜心卷得更紧实,更有卖相,母亲准备用绳子捆起来。我那个时候已经上小学,已经能够帮家里干活了。于是冒着初冬的寒气,踏着清晨的白霜,妈妈领着我们姊妹俩拿了从棉花杆上抽下来的皮条来到地里。那棉花皮条像一条褐色的长带子,长短刚刚够把白菜绑上一圈,简直就是绝佳的搭档。我们轻轻弯腰,或者深深鞠躬,细细的棉花皮握在左手手心,右手拿着另一端,
绕着大白菜周身逆时针转一圈,刚好能够和另一端合拢。有的棉花皮没抽好,比较短,用两条绑个死结合二为一就可以了。只一两分钟,刚才叶子散开像开怀解带醉汉一样的白菜,经过我们母女一番精心打扮,活脱脱一个矜持的女子,身着青白绣袍,妖娆而多姿了。直起身子,满地绑好的大白菜就像女子十二乐坊里待舞的绿衣姑娘般惹人爱怜。
这时候,母亲的头发上额头上也跳动着细密的晶莹的水珠,在晨雾里透过淡淡的阳光,闪闪发亮。没有劳动的苦和累,只是叫嚷着看谁绑得快绑得好,我和妹妹各自在妈妈慈爱的目光中卖弄自己的技巧,这宁静自由的时光便氤氲成一副儿时故乡之冬的美丽画面。
记忆中,故乡之冬还是是温软惬意的。不说母亲在灯下纳鞋底,也不提雪天滚雪球捕鸟雀,单是挂在村落里雄伟壮观的粉条长阵,就足以骄傲一冬的岁月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,身在渭北的故乡人就是在最寒冷的冬天制作红薯粉条的。整个过程需要一个冬天那么漫长,从深秋时节挖红薯,洗红薯,然后在机器中打红薯渣,在池中过浆,沉淀,这就制作好了红薯淀粉,俗称“粉面子”,细腻柔滑,晒干,可以做美味的凉粉。
三九寒天终于如期而至,半村的人都来我家挂粉条,烧水,和面,用大勺子舀上倒在漏盆里往烧开水的大锅里下,丝丝粉条就在锅里来回游动了,这时父亲手持一根半截木棍,伸到水里一捞,那一杆粉条犹如蛟龙出水,热气腾腾地就被挂在事先栓好的两行铁丝上,一杆,两杆,不一会儿的功夫,铁丝上排满了挂好的粉条。经过夜晚几次泼水使粉条冷冻,第二天每家的院子里,村道上,长长的粉条阵便如巨龙一般蜿蜒曲折,看不见头,望不见尾。早上放学的一群孩子们便在长龙里穿来穿去,如铃的笑声回荡在粉条长龙阵里,好不惬意。一挂一挂的粉条硬邦邦的,只有等中午太阳红了,暖融融的,冻了一晚的粉条才开始消融了,一滴一滴的冰溜子融化下落,直到完全晒干,粉条打着卷曲一折就断。每每这个时候的夜晚,是最温馨也是最解馋的时刻,我们围着火炉,一边听父亲讲神仙鬼怪的故事,一边拾起地上断了的一根粉条,把一端放进红红的炉火中,只听“吱吱吱”几声,坚硬细瘦的粉条瞬间变白而且膨胀,吃一口,松脆糯甜,还伴着“咯吱咯吱”的曲调,满口的幸福滋味。
当然,还有最喜欢筹备过年了,这在渭北农村是极其盛大的事情。腊月中下旬,村落里那些此起彼伏、前后呼应的杀猪宰羊声总悠悠扬扬地传来,和谐的邻里相互邀请,其乐融融地围在一起分享自家的喜悦。能干的母亲在物资匮乏的时代总能变着花样弄出一桌美味,尤其把自家的那盘白菜炖粉条是全村老少的最爱,再加上自家圈养自家宰杀的猪肉,母亲愣是给我们炖出一个和睦祥悦的盛年来。
如今,二十多年过去了,时间一点一滴地厚重,对故乡之冬的怀念也一日一日地深刻起来。城市里空调房温暖如春,但我却始终怀味母亲和我在寒天冻地里绑白菜的自由惬意;城市里饮食丰盛,可我却执拗地认为,父亲在炉火中烧焦的红薯粉条和母亲炖的白菜粉条,才是这世间最温软最美味的佳肴珍品。
优美散文欣赏——杏花的遐想
杏花的遐想 作者:
